——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
——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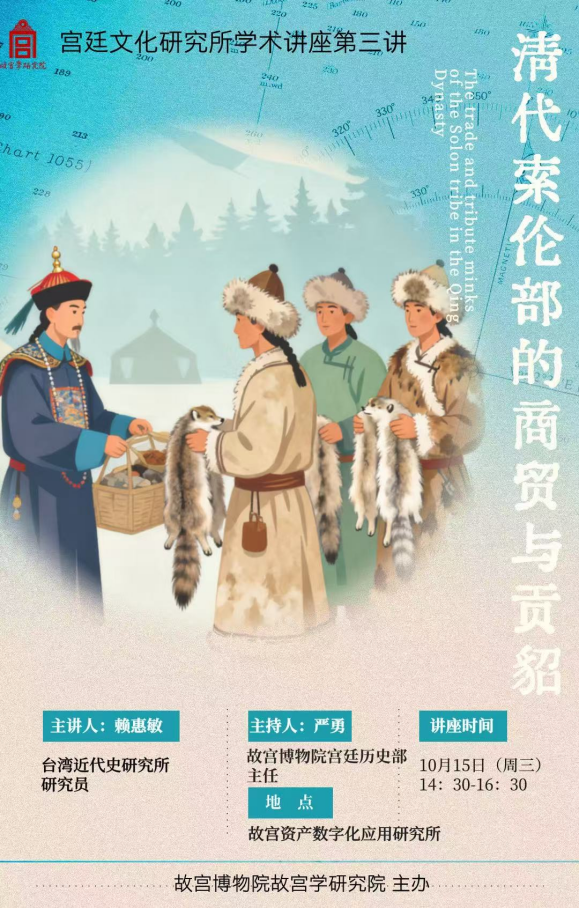
“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海报
2025年10月15日下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主办、宫廷文化研究所与数字与信息部承办的“宫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台湾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以牲畜与毛皮为线索,探讨索伦部的商贸与向清廷贡貂的情况。讲座由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研究馆员严勇主持,来自故宫学研究院、宫廷历史部、图书馆等部门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研究院的师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主讲人赖惠敏研究员
赖惠敏,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2009-2014,2019-2022),主要从事清代宫廷史、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著作:《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中华书局,2020年)、《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乾隆的百宝箱:清宫宝藏与京城时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等,发表学术论文95篇,其中《乾隆的百宝箱》一书获台湾“科技部”2014年杰出研究奖。

主持人:严勇主任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以“清代索伦部的商贸与贡貂”为主题开展学术讲座,依托台湾公藏档案、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满汉文档案及中俄关系历史文献,系统梳理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代索伦部贡貂制度的运行、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清代东北边疆治理的复杂图景。
一、贡貂制度:清代东北边疆的“制度纽带”
讲座开篇,赖惠敏研究员指出,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东北边疆秩序趋于稳定,贡貂制度逐步完备。黑龙江、吉林及唐努乌梁海等地区陆续被纳入贡貂范围,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部族成为贡貂主体,其中黑龙江地区因山林繁茂,成为清廷倚重的貂皮产地。
从档案记载来看,贡貂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与数量规范。据《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载,乾隆四十三年索伦贡貂人数和等第,索伦、达斡尔壮丁3366人,需贡三等貂皮4张;四等貂皮68张;五等貂皮437张;黄貂皮2857张,共3366张。食钱粮的鄂伦春壮丁269人,贡黄貂皮269张;而需给价收纳的鄂伦春、毕喇尔部族,三等貂皮1张,每张3.5两计价,四等貂皮151张与五等貂皮188张,每张3两计价。内务府与户部共同检验貂皮的等级,貂皮的质量依照等第进行区分,分为:头等貂皮(满文:ujui jergi seke)、二等貂皮(满文:jai jergi seke)、三等貂皮(满文:ilaci jergingge)。
值得注意的是,贡貂数量受外部战事影响显著。赖研究员通过对比《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等资料发现,雍正十一年(1733)因索伦部牲丁被大量征召参与清准战争,贡貂数量骤降至100余张;乾隆四年(1739)清准战争暂歇后,数量才逐步回升;乾隆二十年(1755)战事再起,贡貂数量再次锐减,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南疆后才恢复稳定。
二、俄商来华:边境贸易的“机遇与乱象”
《尼布楚条约》不仅确立了边界,也开启了中俄边境贸易的篇章。讲座中,赖惠敏研究员依托《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1653-1966)·清代编》等文献,还原了俄商来华的具体路径与贸易细节。
俄商来华主要通过三种名义:一是“奉命出使”,借外交名义获取清廷路费资助,如康熙三十年(1691),俄商以“察罕汗使臣”名义率90名商人入境;二是“伴随使团”,沙皇在给使节的训令中明确要求搜集商业情报,1693年伴随伊兹勃兰特使团的俄商达80人,使团总人数更达392人;三是“国家商队”,1689-1727年间,俄商前往北京贸易31次(26次成功入境),前往齐齐哈尔等地22次(19次成功入境),1706年格里戈里·奥斯科尔科夫率领的国家商队,仅獭皮就携带8000张,1715年斯捷潘·谢诺托鲁索夫商队更带来马400匹、牛100头。
俄商输入的商品深刻影响了当地部族生活:马匹满足了鄂伦春人山林狩猎的交通需求,牛只助力达斡尔人的农耕生产,银鼠皮、狐皮、獭皮等则补充了布特哈人狩猎所得的不足。但贸易也滋生诸多乱象:商队人数常超200人上限,最多时达四五百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还发生监督官阿尔法欠银2475两、商人赊欠纠纷等问题;俄商斗殴滋事频发,1704年沙皇不得不专门谕令“严禁商人酗酒斗殴,违者缚以铁索拷打”。最终,清廷因财政负担过重与秩序混乱,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止俄商来京贸易。
三、边境互动:索伦部的“生存与治理困境”
讲座第三部分聚焦索伦部的族群迁徙与边境治理难题。赖惠敏研究员介绍,清朝入关前,索伦部原居黑龙江北岸,因俄罗斯势力东扩南迁至嫩江流域,清廷以“索伦”为黑龙江将军管辖部族的统称,设布特哈衙门管理鄂伦春等狩猎部族。
尽管清廷严禁越界贸易,但边境族群的经济依存关系使走私屡禁不止。档案记载,索伦、达斡尔民众常以捕貂为名,前往俄境尼布楚或额尔古纳等地交易,貂皮因双方严格管制成为高利润走私品。乾隆三十三年(1768),就有客商赵九锡、程开吉私买带俄式烙印的狐皮、羊皮及玻璃镜等货物,被清廷交刑部审理。此外,俄方边民越界捕猎也冲击索伦部经济,清廷虽多次通过理藩院交涉,但因跨境社会网络交织,始终难以在维护条约与资源竞争间找到平衡。
讲座尾声,赖惠敏研究员强调,以往研究多从外交、军事角度解读清代边境政策,而本次通过《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清宫内务府奏案》等一手资料,从贡貂制度与商贸互动切入,更清晰地展现了清代东北边疆的族群关联与治理逻辑。索伦部的贡貂不仅是“赋税义务”,更是清廷确立统治的纽带;俄商贸易既带来经济活力,也暴露边疆治理的短板,这些历史经验为研究清代民族关系、边疆政策及早期中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次讲座以扎实的档案考据与清晰的逻辑梳理,为听众呈现了清代索伦部商贸与贡貂制度的全景,也为相关领域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图书馆
图书馆
 视听馆
视听馆
 故宫旗舰店
故宫旗舰店
 全景故宫
全景故宫
 v故宫
v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