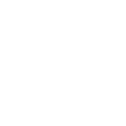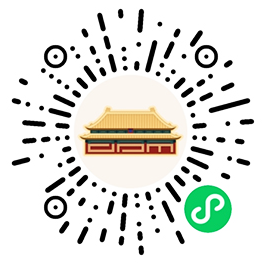章草书,广义而言是汉代通行的隶书草写法,即隶草;狭义而更为准确地说,是在隶草的基础上进而规范化的一种专门书体,即经过规范、美化的隶体草书。章草书盛行于东汉末期,历经魏晋时代而渐成衰势,隋唐以后罕有书者,故是一种古代书体。至元代,随着书法艺术的演变而出现了复古倾向,赵孟頫诸人遂复活了这一古书法,这对楷体之行、草书的艺术表现有较大的影响。正因这是一种曾经盛行又被历史长河几近湮没的古书法,尽管曾在当时产生过如汉张芝、西晋索靖等一批著名的章草书家,但迄今绝少有墨迹留存,至多在历代刻帖中辗转翻刻而留有数种帖书。故宫博物院新近征得的原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书《出师颂》恰弥补了这一历史性的缺憾,故本文略述章草书之由来以及古代章草书家之简况,以便从中看出隋人书《出师颂》的历史、艺术价值。
一、汉兴有草书
“汉兴有草书”,这是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的结论。东汉时期草书更为盛行,并在实用的基础上愈来愈成为一种为书法而书法的专门书体。由于东汉中期后兴起了热衷于草书的社会风气,东汉末的赵壹作了一篇《非草书》,非议草书的盛行,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关草书发展状况和种种表现的宝贵资料,是书法史中一篇早期的理论文章。赵壹指出:“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这是对草书产生原委的评释,并作了引申和发挥,为一些后来者所赞同。如宋张栻说:“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事实上,每一种文字都有快速、潦草、简易的写法,都可以看作是广义的草书。但从隶书的草写开始便有所不同,因为隶草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为一种专门的书体,即由隶草演为规范化的章草书。赵壹曾说,草书“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但是,当时草书已不仅仅“示简易之旨”,而是需用很大功力才能实现所预期的效果。正如赵壹在《非草书》中描述的:“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罢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此外,草书也不再是“非常仪”的潦草、简易的写法,而是通过“删难省烦,损复为单”的实践,逐渐总结经验而规范为有常仪的专门书体。这说明,由隶草演为章草,主要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追求书法艺术表现的结果。赵壹此说因其不知本属“伎艺之细者”的书法已经成为皇者、大者之事,且即将进入自觉阶段的书法艺术了。虽然如此,草书仍保持着“趣急速”所形成的基本特点,一是简,一是连。简指字的结构或笔画的省减,连是书写笔画的纠连。至于字与字的纠连或是数字相连的“一笔书”则是今草而非隶草的特点。关于章草书的定名有三种传说:一说汉史游创章草而书《急就章》;二说汉章帝创章草;三说是汉章帝好草书,准许以草书用作章奏事。这几种说法不过是“圣人作”的旧说,不一定符合草书之所以产生的实际情况。许慎所说的“汉兴有草书”应当指的是隶草,是为书写便利、急速的广义草书。在西汉早期的简书中,凡书写潦草、流便者皆可视作是最初意义的隶草。随着隶书成熟的过程,也开始了章草书形成的过程。章草书虽然源于隶草,但与隶草又有显著的区别。一是章草书的“解散隶体粗书之”,即在隶字的结构上再次减化,将隶字方折的笔画易为圆转,以便于书写;二是保持了隶书特有的波磔笔法,但将“一波三折”的波捺笔易为比较崭绝的奋笔,以取“赴急”的促势。西汉简书中的《神爵四年简》(公元前58年)已粗成笔法。至东汉初的武威医药简则已具章草书体模,表现出波挑之势和折锋使转的章草法度。类似的东汉草简很多,从时间上看早于汉章帝时代,证明了传说中的章草之创不可尽信。虽然如此,但这几种传说也证明了章草书在汉代盛行并得到皇帝及文人们的喜爱和认可,同时反映了他们在章草书的规范、推行中所起的作用。
二、东汉的章草书
东汉的书法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鲜为人知者,他们创造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碑书法或简帛书法作品,却绝少有姓名的记载,仅有如《西狭颂》的书者仇靖、书《郙阁颂》的仇绋、书《衡方碑》的朱登等有姓名流传于世。《华山碑》碑末题:“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但是,是为郭香察者书,还是为郭香者“察书”?金石学家们历来争论不已。更多的汉碑则无法知道为何人所书,更不用说简帛书的作者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类书法家大多是地位低下的书佐、书吏,多是职业书法家,不为文献所记载。另一种类型的书法家则如赵壹所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杜、崔、张子即东汉时号称“草圣”、“书圣”的杜度、崔瑗、张芝,是官僚、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士中的擅书者,且恰恰大都擅长章草书。这类书法家,据文献记载还有曹喜、王次仲、蔡邕、师宜官、刘德昇、粱鹄等人。造成书法家们这种区别的原因自然是当时的社会。对于促进书法史的发展,他们各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量的简帛书、碑书曾促进了隶书及草书的发展和成熟,并极大地提高了书法的表现能力。在此基础上,士大夫文人较参与绘画艺术早一个时代而登上了书坛,他们在总结和深化书法的艺术表现方面曾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从而促进了书法艺术向自觉方面的转化。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士人们的参与,书法艺术很难完成从自在向自觉艺术的转化。下面从书法家的情况和当时的书法理论著述两方面加以说明。
杜度,原名操,字伯度,汉章帝时为齐相,擅长章草书。唐韦续《墨薮》记:“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又唐张怀瓘《书断》称:“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这些记载并不准确,却反映出章草确实在章帝时代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了杜度这样著名的章草书家。魏晋人评其草书:“有骨力而字画微瘦”,“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评语是统一的,说明杜度已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尽管每个人写字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联系赵壹所说当时的书法家们“夕惕不息,仄不暇食”的极诣追求,就可想见所谓个性特点中即包含着书者对艺术表现的追求,从而表现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内蕴精微的艺术风格特点,这在书法史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崔瑗(78— 142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人,官至济北相。尝从杜度学章草书,世人并称“杜崔”。他的草书“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可见当时的章草书已愈趋规范化的严密和工丽了。《后汉书》中有其传,他的《草书势》为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全文引录,这是书法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书法理论文章,并且是专论草书的文章。文章很短,但提出了三个在当时最重要的书法理论问题,标志着由写字而书法的最终完成。一是形与情的对应,即书法艺术的情感特征,这在全文中占突出的位置。如:“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前二句讲章草书“字字区别”、“笔断意连”的结构形态,因其似珠连而未联,故“畜怒怫郁”,又因其意连而“绝而不离”,故“放逸生奇”。尽管文字简略,却已经讲出了形与情相结合的情态特征。二是形与理的对立,即书法艺术的理性内容。“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书法中有丰富的形态表现,可以离方遁圆,但俯仰须“有仪”,也就是方圆变化中的规矩,所以称法象,即方圆、刚柔、正攲等对立而又统一的中和仪象。因此,法与象的统一,也就是形与理的统一,理即中和之美的观念,是书之法所由建立的根本的理性思想基础。三是讲“纯俭之变,岂必古式”的进化论。其意本指章草相对隶书的简瘦,但这种对“纯俭之变”的态度却反映出书法自觉意识的乍萌,传达了处于书法艺术表现千变万化之时代的艺术家们欣喜与自信的心情。而且,在当时的一股复古、保守的社会风气中,对书法艺术的兴起也有如赵壹诸人的非议。可以认为,崔瑗的《草书势》一文虽文辞简省难解,却触及了书法艺术领域内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有了基本的解释,这对后来的书论影响极大。
张芝(?—192年),字伯英,敦煌渊泉人。擅章草,三国人韦诞赞其书“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谓为“草圣”。可以想象,在东汉末年以张芝书为代表的章草书已发展到极致的水平。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云:张芝“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练染),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此后,人们就习惯地将学习书法称作“临池”。又说:“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研究者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表面看,似指因没有时间而草草书此之义。但另有一解,是说因为没有时间,故不能写出好的草书。两说均有道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草书早已不是赴急之用的那种草字了,而是需经“临池”后方能掌握的一种书体,从根本上划清了写字与书法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张芝的草书不仅精熟过人,并且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具有一种似得道后的自由,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表现。
东汉的书法家已无墨迹传世,仅历代刻帖有所传刻,且真赝混杂。例如北宋初的《淳化阁帖》刊刻了汉章帝、崔瑗、张芝三人的几份帖,到北宋中期即陆续被鉴评家们鉴为伪帖。其中,汉章帝的《千字文断简》书作章草体。有一种说法是因汉章帝喜爱并善此体书,故名章草。然黄庭坚说:“《章草千字文》,集书家定为汉章帝书,缪矣。”他的理由是《千字文》系南朝周兴嗣编次的,“章帝时那得有之?”据《梁书》等书记载,梁武帝萧衍为教诸王书,命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中摹拓一千字,每字片纸,然后交周兴嗣编为韵文,此即《千字文》的产生时代与过程。以后,《千字文》就成了识字、习字的范本,也是历代书家所喜书的文字题材。黄庭坚的考鉴意见是正确的,是编次《阁帖》的王著犯了误定的错误。大概是因为他相信汉章帝善章草,故将这一《章草千字文》归在了汉章帝的名下。这种误定的现象常常是因作品与某书家有着某种联系,或出于臆测,或出于伪定欺世,而将作品归于某书家名下,在历代的法书鉴定中都有这样的例子。《阁帖》中又收有张芝的《冠军》等六帖及崔瑗的一帖。宋米芾鉴定张芝六帖说:“后一帖是,前五帖并张旭”,又以为崔瑗一帖是齐梁人书。张芝的《冠军》等前五帖及崔瑗的一帖皆属今草范围,张芝的最后一帖《秋凉平善帖》为章草书。米芾没有说出更具体的鉴定意见,宋代也有和他持大体相同意见的人。不论宋人的鉴定意见如何,这里牵涉到一个以书体演变形态为根据断代的问题。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引述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说:“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然而,张怀瓘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以为张芝是首创今草者,并且“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是说,连绵草书也是张芝的发明。张怀瓘的这一看法影响很大,今日仍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南朝王僧虔的《论书》中曾说:“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可见,自欧阳询以往,认识是统一的,即西晋以前没有楷体草书的今草出现,更不可能有连绵草书的形态,连绵草书是在唐代才出现的。因此,鉴藏家米芾是有眼光的,也是熟悉书法史的演变情况的,他以为张芝以章草书写的一帖为真,其它五帖为张旭书是有些道理的。又崔瑗的一帖虽为今草,但较张芝的五帖要古拙一些,因此被他判为齐梁人书是既从书体也从风格上的综合判断。可以说,没有对书法史知识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对一些古法帖进行这样的鉴定判断。
三、魏晋时的章草书
魏晋书法总体来说是处在由隶书到楷书的渐变发展过程中。楷书是沿用至今的字体,因此,这种转变便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隶书仍旧是当时通行的书体,但已明显趋于末路之势,同时,章草书也渐呈衰败之势。另一方面,隶书逐渐向楷书演变,形成楷法兼隶意的八分楷法之书。在此基础上,行书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从出土的魏晋简牍或传世的草书名迹看,多类古隶草,并不强调章草书式的正规写法,说明行、草书也随着楷书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这可从魏晋时的一些著名书家处得到清楚的反映。
皇象,吴国人,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官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章草书。他的草书与严武的围棋、曹不兴的绘画、宋寿的占梦、郑妪的相人、赵达的法术等并称“八绝”。唐欧阳询在《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一文中说:“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羲之)并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是说皇象的章草与张芝并胜,肯定了皇象的书史地位。皇象书的《急就章》是古章草的典范之作,有明刻的“松江本”传世。《急就章》原名《急就篇》,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史游编纂的字书,历代书家多以此为书写内容,而以皇象的章草书《急就章》最为著名。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记》云:“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当时的章草书就类似这种情况。草书原为赴急之用,但章草往往点画省略,异形难识,反而失去了赴急的作用,而成为专门性的书体。一方面,皇象的章草书具有古朴、典雅和规矩浑成的特色,成为后代宗法的典范;另一方面,与魏钟繇的三体书比较,其显然还是前代书法的集成和总结,不是开拓新风的类型。
在西晋书法中,变化显著而影响最大的是草书的演变,即由章草书演化为一种称为“草藁”的书法。唐欧阳询称汉魏、西晋并是章草,到东晋时才有今草产生,这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但欧阳询忽略了由章草至今草间的过渡,即草藁书法的出现,这发生在西晋时期。西晋著名的书法家无不善长章草书,当时人称“一台二妙”的索靖和卫瓘,是因都在尚书台任职,又都是以草书知名的书法家。但索靖主要继承汉魏以来的章草书体,卫瓘则长于自由挥洒,创造了“草藁”新体。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甘肃敦煌人,汉末著名书家张芝之姊孙,曾任雁门、酒泉太守和左卫将军,人称征西或征南将军。章草书巨迹《月仪帖》(又名《十二月朋友相闻书》)相传为索靖所书。在《淳化阁法帖》中刻有他的《皋陶帖》和《七月廿六日帖》等章草书作品。他曾形容己书字势为“银钩虿尾”。虿是蝎类毒虫,尾部上卷呈钩状,是说其字的勾挑笔皆驻锋趯出,为遒劲的状态。但这一特点在上述诸帖中都不明显,而在明初宋克的章草书中则可见这种笔法。索靖的章草书只从形态上小变,南齐王僧虔说其是“传芝草而形异”,他基本上是张芝书法的继承者。
卫瓘(220—291年),魏晋著名书家卫觊之子。其子恒、宣,孙璪、玠,孙女铄,皆是两晋时期的书家。其中卫铄世称卫夫人,王羲之早年曾从其习书,可见卫氏家族在书坛的地位与影响。据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按唐张怀瓘《书断》所释:“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藁。”这种解释类似现在所说的草稿,但用来说明卫瓘的“更为草藁”却是不恰当的。在《淳化阁法帖》中有卫瓘的《顿首州民帖》,粗看仍似章草书,然笔画波势很少,体势流便散落,张怀瓘评其书“率情运用,不以为难”,则是很合宜的,这才是卫瓘创造的草藁书法。草藁本来义同草稿,但在这里用作一种特殊的书体概念,既不同于规范化的章草书体,又是在章草书的基础上加以变化,主要是减省了章草书的波磔笔法。本来草书是为赴急之用,但严格的章草书体反而走上了匆匆不暇而难以草书的道路。卫瓘“更为草藁”,可以认为是回归到古隶草了,但它又不同于汉代的古隶草,因为它又与钟繇的行狎书即相闻书结合起来,是一种隶与楷、行与草相间的形态,是只存在于西、东晋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书法表现,当时称为草藁。现在留传于世的、相传为最古的名家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也是这种草藁。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上海市)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平复帖》是他书写的信牍,书法在章草与今草之间,书风古朴自然。草藁是从章草书中演化出的行、草间参的先进书体,它是产生东晋王羲之、王献之行草书的先导,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作用却是极大的。
四、二王书法新风
随着西晋东迁,一些士族大家渡江而南,于是热衷于书法的风气以及原流行于北方的钟繇、索靖等名家书迹也随之到了江南。东晋的士人较之汉魏人士更热衷于书法,近代人马宗霍《书林藻鉴》曾分析原因说:“俗好清淡,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这是在东晋士人中流行的风气,又化为晋人书法的特点而风行。在以往的书法创作中,包括钟繇、索靖在内,大多注意的是书体或书法形态的特征表现,比如崔瑗的《草书势》,基本还是对草书表现形态的描述或赞美。而在这时已酝酿着一种人、书合一的艺术思想,如汉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或钟繇所言“书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将书法的表现,直接、贴切地与人的思想、情感、生活联系在—起,以体现人之风貌,则是东晋书法表现的主旋律。因此,古章草书更加不孚人望,代之而盛行的是今草和行书,除由隶而楷的字体变化因素外,又加上了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因素,其代表人物便是二王父子。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渡江后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氏家族一向爱重书法,“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这个王廙是羲之的叔父和其早年的书法老师,曾携索靖帖过江。羲之的另一位老师是卫夫人(铄),相传著有《笔阵图》。在这样的环境下,羲之很早便受到了书法艺术的薰陶,接受的是张、钟、索、卫一系的汉魏书法。但是,“亡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这是羲之四世族孙王僧虔《论书》中的记载。王洽为羲之同族兄弟,小羲之20岁。所谓“变古形”,实际上羲之是第一人。这样,羲之的书法便有了早晚期的变化,即所谓“犹为未称”的早年书与“末年多妙”的不同。世传羲之的书法作品都是楷、行、草体书。其中楷书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等,皆以宽稳精秀为主体风格。其行书作品以信牍之类的法帖最多,以著名的《兰亭序帖》最为典型。草书则以《十七帖》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的草书集帖,因卷首有“十七”二字得名。他的行草书变化最丰富,以清峻潇洒的风格为主。其书法作品传世较多,但无一真迹墨本,除刻拓本外,墨书则多是摹、临之作。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羲之第七子,曾官中书令。幼学父书,其后则创新法,善楷、行、草书。唐张怀瓘《书议》说:“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这段记载应当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也记载了献之的艺术进化论思想,其中有一段献之与羊欣讨论张、钟、二王书法的对话,献之以“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的话相答,体现了一代胜于一代的思想。虞稣则总结道:“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这既可作为西晋以往与东晋书法的区别,也可看作二王父子间的差异,正如虞龢所说:“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从献之关于改体的一段话看,章草书未能宏逸,主要是因矩度过严的“局而执”。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是说羲之的变古形,亦不免于朴茂雄强的古质风意。但不可一律地这样看待羲之的书法,如《兰亭序帖》就更具多姿多彩的艺术性。张怀瓘的《书估》在同样引述了献之的话后,加了一句“逸少笑而不答”,是父亲对儿子的嘉许态度,嘉许他懂得了自己在暮年时已经摸索出艺术创作发展的道理。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竞创新风,各成典型,是东晋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风气的写照。当时的庾、郗、王、谢等门阀家族皆以书法世代相传,如庾亮、庾翼,郗鉴、郗愔、郗昙,谢尚、谢安及羲之家族祖孙都是东晋知名的书法家。对羲之所创新书风,庾翼就曾忿而不平,扬言“须吾还,当比之”。这反映了晋人书法竞相争妍的状况和“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的艺术创作原则。同为王氏家族子孙的王珣(350—401年),他的《伯远帖》书法潇洒古澹,类羲之的《姨母帖》,仍存魏晋古风。王荟的《疖肿帖》,见于《万岁通天帖》中,书法洒落虚清,不拘古法。按王荟为王羲之平辈兄弟,王珣为子侄辈,古质与今妍的书风和书家的生年与辈分正相颠倒,说明晋人书法的不拘一格。尽管如此,东晋书法总体上是趋于“今妍”的表现。所谓“今妍”,固然有秀媚多姿的形态特点,但其本质则不仅在于秀妍的风姿,而在于这风姿中体现的人的风貌和神韵。正如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中所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无论其褒贬是否公允,其将二王书与谢家子弟、河洛少年相比拟,则正是晋代士家子弟风神的写照。二王书法是书法之形貌与风神的完美统一,从而成为以后历代书法的典范。
综上介绍,可以看出,东汉末至隋唐之前是书法史上演变最烈、书家繁盛、新书体、新风格不间断地推出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从中还可以看出,在诸多变化中,章草书几乎是其中每一变化的标志性书体。在章草书出现并逐渐确立的过程中,汉末张芝、杜度,两晋索靖、卫瓘等一批书法史上有文献记载、有作品的早期书法家的出现,标志着书法艺术由自在阶段向自觉地艺术创造阶段的转化,同时确定了书法艺术形态表现与艺术内容传达的基本特征。自魏晋以后,伴随着由隶书而楷书,由隶草、章草而今草、行书的演变过渡,章草书至少在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章草书“解散隶体”的“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对楷书一体的形体确立有重要的参照、启示作用;二是章草书的规范、美化形态,不仅对楷书,且对楷书之形、草书的出现、确立同样有重要的参照、启示作用。当楷、行、草书作为新书体出现后,也随之出现了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等又一代著名书法家,书法史上并称为“钟王”。但他们在创造新书风时,始终在“古质今妍”的辩证中展开,甚至隋唐以后的书家创造各种书体亦大都以创新风又含古意作为高水平艺术的标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所以能持续发展又不断丰富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艺术中的复古倾向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作为一种古书体,章草书虽曾几乎被历史尘埃所湮没,但又终在元代复出,并且为元代以后的书体创造注进了新生的艺术活力。
五、章草书《出师颂》
故宫博物院斥巨资征得章草书《出师颂》。该作品对于研究章草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出师颂》曾历经南宋绍兴、清乾隆两代内府收藏,以其卷后有宋米友仁一段鉴定题跋而被定为“隋贤书”。《石渠宝笈》从其说,也定为隋人书。迄今,经权威书画鉴定家启功、徐邦达、傅熹年等先生鉴定,也确定为隋代的书法作品。综观隋代书法,尽管隋王朝仅存在了37年,但却是书法史中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正如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史论家沙孟海先生指出的:“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变革发展诡奇百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因为隋代书法作品传世绝少,在墨迹作品中除一些写经外,著名者如隋僧智永《真草千字文》已是晨星之一。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将隋代书法置于其上下时代中加以综合比较,这也是沙先生结论中指出的。如本文前述,由“汉兴有草书”,至章草书的规范、确立,传为吴皇象《急就章》、西晋索靖《月仪帖》的出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章草书的规范,或者说是隶草的“正体”。按事物发展规律,一旦有“正体”,则变化必然随之,于是有了两晋卫瓘《顿首州民帖》、陆机《平复帖》的所谓“草藁”书,这是对规范性很强的章草书的“解散”和“粗书之”。因此,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讲:“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其时是章草书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因“草藁”书的出现使章草书受到冲击而渐成衰势。如果我们将《出师颂》置于卫瓘的《顿首州民帖》和陆机的《平复帖》之间加以比较,则不难看出《出师颂》的章草书介于两者间,既没有前者的规范,也不似后者更为随意、率真。
因《出师颂》无名款,所以在历代著录中有不同的说法。最早的一种说法当属北宋人黄伯思,其《东观余论》认为是南朝梁书法家萧子云所书。萧子云,字景乔,书法师钟、王,善草、行、小篆书。黄伯思评云:“萧景乔《出师颂》虽不迨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其中“正隶”应该不是指隶书而是正体隶草,即章草书。黄伯思认为《出师颂》的章草书已经离魏晋人的章草书有了较大距离,只是尚有古体遗风。接着他又说:“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他道出唐宋以后古章草书渐为湮没,正说明《出师颂》应是唐以前的书法作品。故黄伯思所说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即《出师颂》书字有古意,但又不同于魏晋时的古章草,以其为南朝梁萧子云书则确定了书写的年代。南朝梁至隋不过数十年,因之与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则大体可称不谋而合。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研究《出师颂》时指出:“论书法很古厚,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也是以其书法的特点、风格断为隋人书。
至于明清著录书中称为西晋索靖书,或如黄伯思称为梁萧子云之书,一般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因其无名款,往往令人觉得是一种遗憾,故根据作品的书体、书风臆定为某名家书,其后便代相沿袭为某家作品。这种情况在古代绘画作品中也时常发生,例如“牛必戴嵩,马必韩幹”,就是将无名款的画牛、画马作品分别归为画牛名家戴嵩、画马名家韩幹名下。其实人们并非真的相信俱为戴嵩、韩幹所画,只是出于看重某作品的一种习惯做法。二是为增重作品的经济价值,将作品的时代尽量前置,并将其定为某名家之作。例如《出师颂》,如果真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所书,则便是索、肖唯一的传世墨迹作品,那么它的历史、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其经济价值恐怕也是迄今以来书画市场难以估量的。其实这种情况,古今以来皆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凡是有书画鉴定眼力者必不会虚听其名而是鉴定作品本身,有名无实者弃之,虚名有实者则凭实而论。故宫博物院征得《出师颂》即为例证。总之,鉴别、鉴定古书画并非仅凭是真是假、值多少钱这样简单的说法。既然类似《出师颂》这样的传世名作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就应将其置于章草书演变史中加以考查,综合辩证古今人的研究,揭示其在书法艺术中的位置,方能确定其所以能为历代所宝重的意义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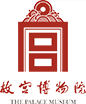
 图书馆
图书馆
 视听馆
视听馆
 故宫旗舰店
故宫旗舰店
 全景故宫
全景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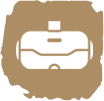 v故宫
v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