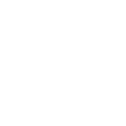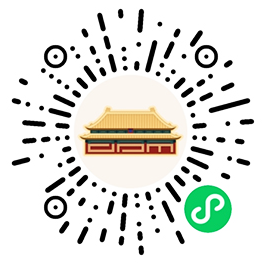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中虹桥景物的探索
《清明上河图》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一般文献所不具备的。认识宋代社会和艺术的发展,对卷中景物内容和艺术表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有益于对作品认识的深化。
例如,虹桥一段是全卷展示的高潮之一。无柱的木构“虹桥”是宋代中期建桥中的伟大创造。开封的无脚桥最少有三座,而当时从开封至江南的运河上更建起了很多此类拱桥。图卷对虹桥的结构作了具体几乎是毫发无遗的图写,以成排的巨木组成拱架,榫卯箍扎的结构飞架于河上。桥两头竖立着四根顶端带有鹤形的高竿,研究者皆认为是风向标,笔者拙见却以为应是华表,是虹桥建筑的组成部分。按华表在古代亦作桓表,据传最早系贤明的帝王树于街衢用以纳谏的竖木,后来演变为纪念或标志作用的柱形建筑,晋崔豹《古今注》中对华表的解释是“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设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衢路也”。桥梁通常处于“大路交衢”,故树以华表,如《洛阳伽兰记》即记载在洛阳南郊洛水上的永桥,南北两岸竖有高二十丈的华表,而且上端“作凤凰似欲冲天势”,可与《清明上河图》的桥头立柱相印证。至于图中华表顶端不是凤凰而作鹤形,则是起于汉代丁令威学道化鹤集于城门华表柱上的传说,故事见陶潜《搜神后记》。桥头华表增长了桥的气势,上河图将这一景象传写下来,为古代建筑史和开封风貌留下形象资料,殊为可贵。
《书画传习录》中对张择端的谬记
张择端生活于北宋末期,其生平历史仅见于画卷后张著题跋。张择端幼年攻读诗书,曾在开封游学,后来转攻绘画,尤精于界画,被遴选入皇家画院,当时宫廷绘画提倡深入细致的观察、精微的描绘和巧妙地表现,《清明上河图》达其极致。张择端是一位有文化、有生活积累、有头脑、有技艺的画家,非一般画工所能比拟。过去我曾发现王绂《书画见闻录》中有“以失位家居卖画为计”的史料。后来有人据此撰文谓《清明上河图》系张择端“失位家居”后所绘,而《西湖争标图》(指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金明池争标图》)才是其在画院时所作,这个结论未免轻率。须知宋代画院画家和社会大多有着密切联系,朱锐、李嵩都供职画院但他们画的盘车图、货郎图完全反映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况且《清明上河图》原有徽宗题签,怎么能在失位家居时所画?该文又进一步推断因其失位家居而《宣和画谱》中遗其名氏,其实《宣和画谱》对徽宗时代的画家除宗室内官外很少为之立传。况画谱编于宣和二年,很可能《清明上河图》尚未画成,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社会生活就一定在院外完成,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书画传习录》中张择端史料不可信之处还在于他把张择端说成是官至翰林承旨,则其身份非供职翰林图画院,而是翰林学士院之高官,实际上张择端是由士子转为画家的,所以“失位家居”也就很难成立。该书又记清明上河图上有金朝皇帝印玺,更与此画流传情况不符。该书张择端材料亦未注明出处。《书画传习录》一书系清嘉庆时阮承咸于书肆发现的一个残本,时距王绂已四百余年,书中有论书论画内容,且“蟫残鼠劫者十之三,帝虎鲁鱼别风淮雨者十之二”,即其残缺及讹传失误部分占去近半,又经过阮承咸的一番补充整理,杂引各书时常随意加以增删,故引用时须谨慎对待。例如该书谈及燕文贵初名肃,字仲穆,起家幕僚,官至侍从,文章事业卓然可观。王绂又谓文贵初为燕王府官(《书画传习录·己集·精敏门》),则将文贵与燕肃混淆,殊为可笑。因此,不加辨析的运用《书画传习录》材料而遽下结论是极不稳妥的。
(作者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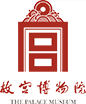
 图书馆
图书馆
 视听馆
视听馆
 故宫旗舰店
故宫旗舰店
 全景故宫
全景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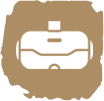 v故宫
v故宫